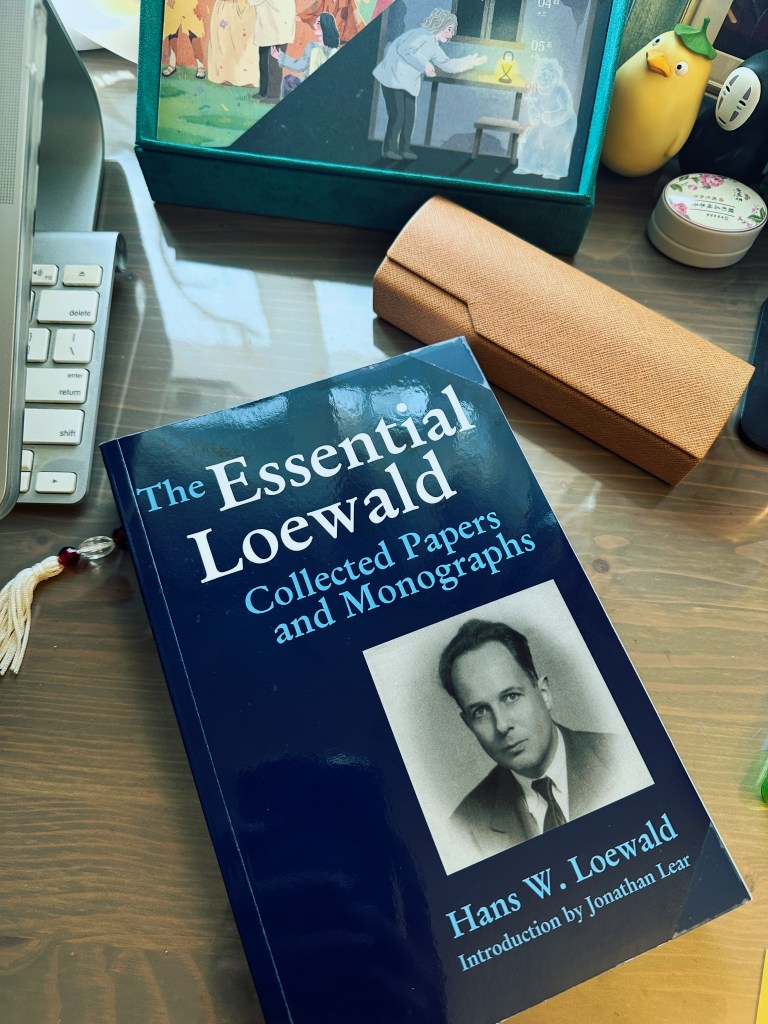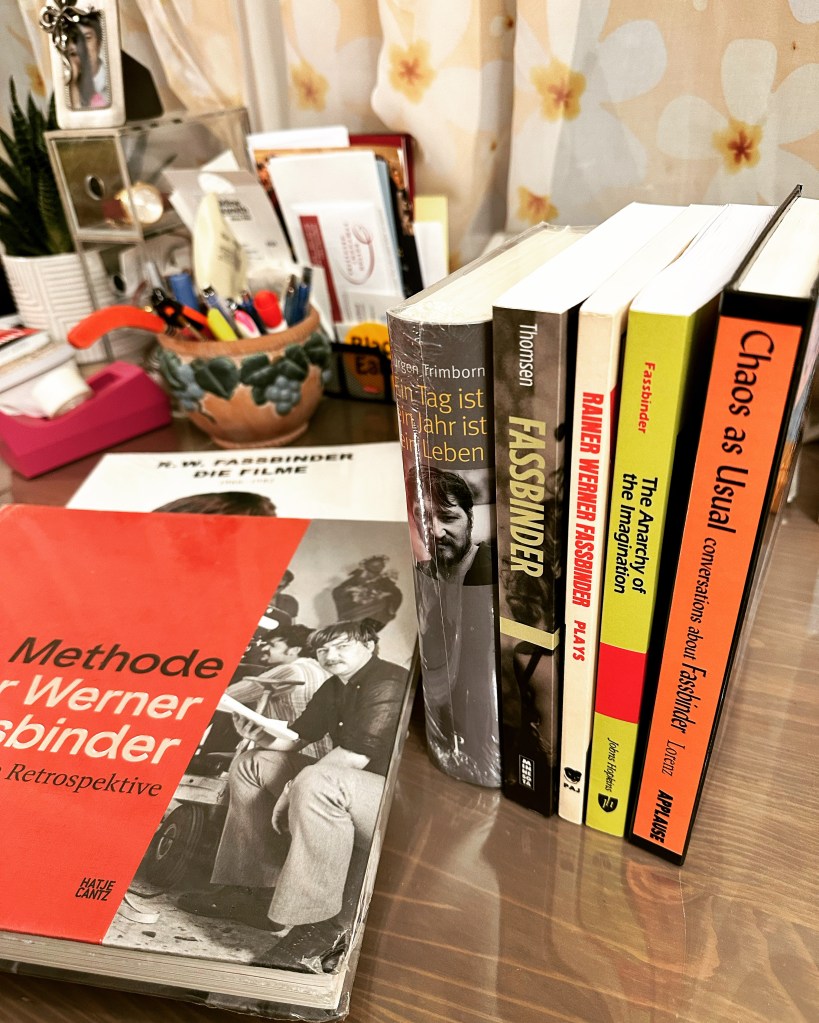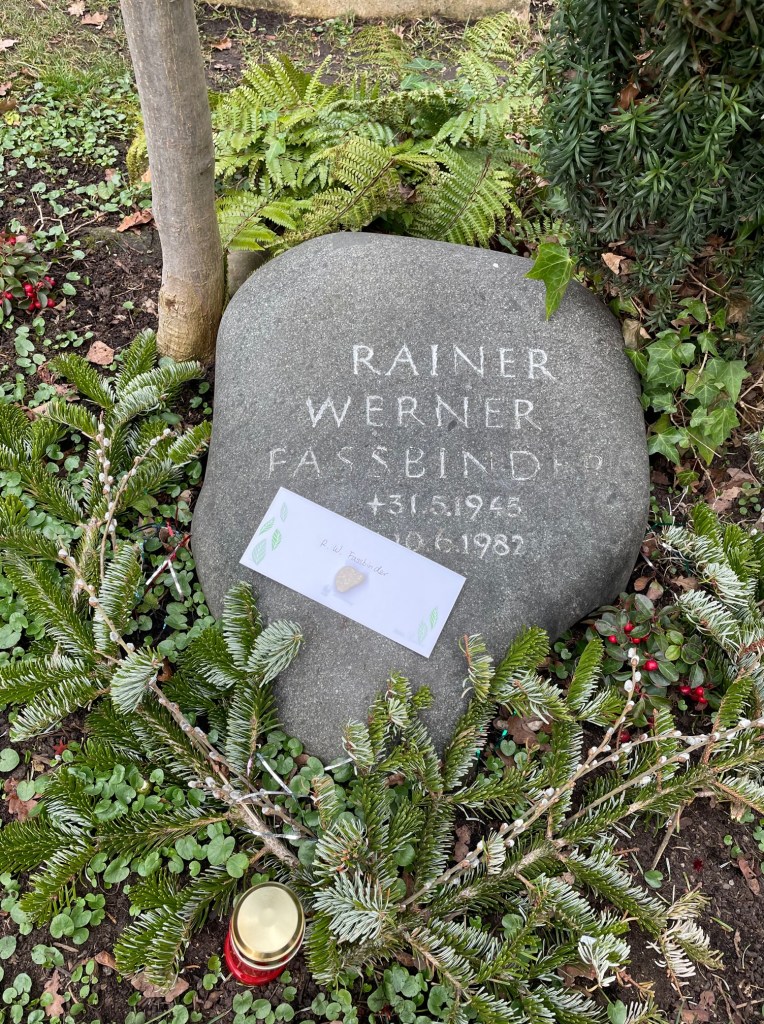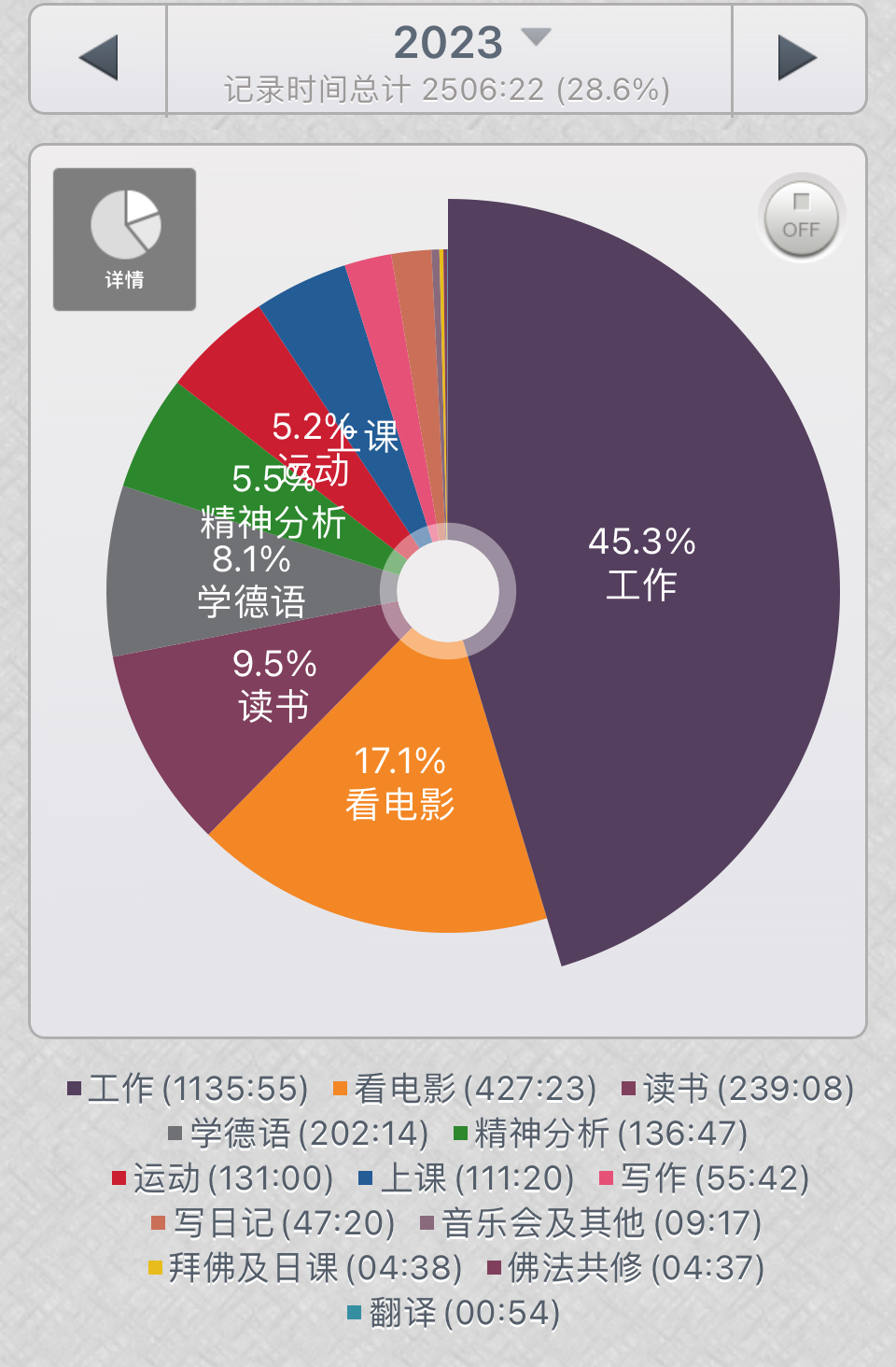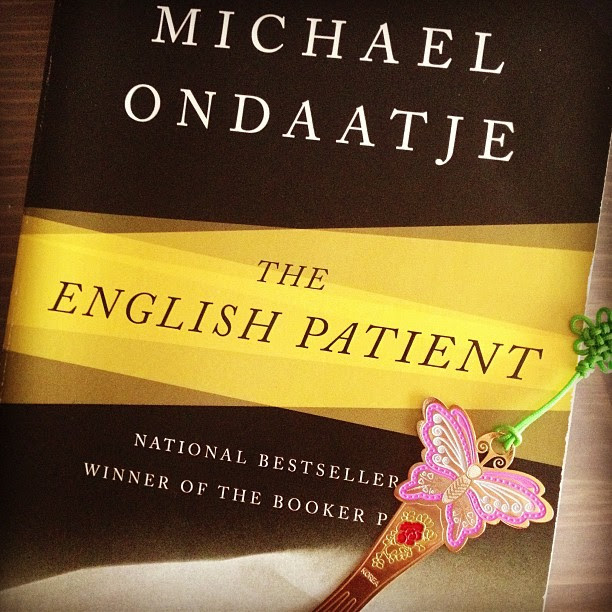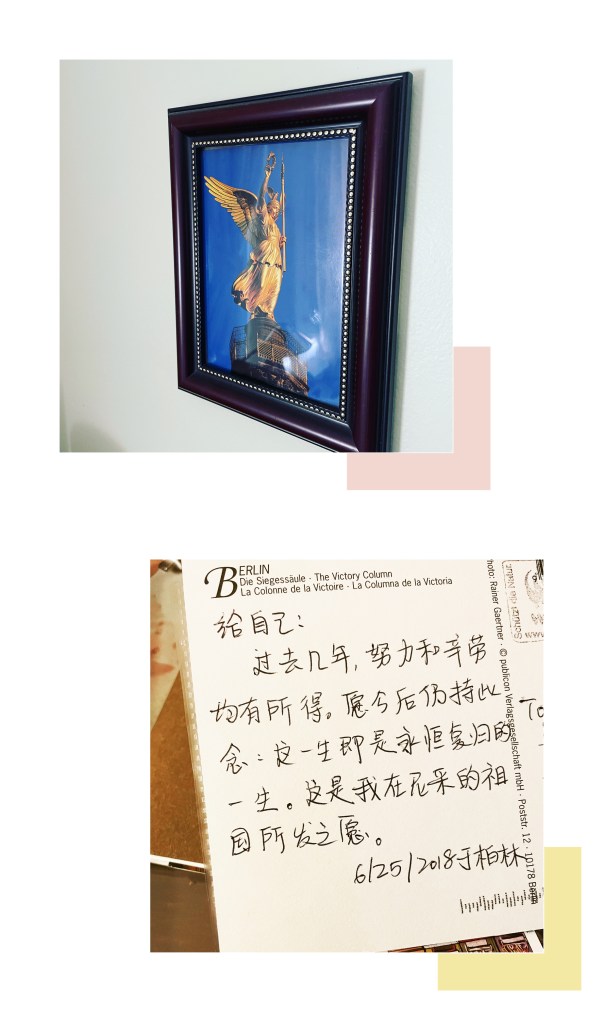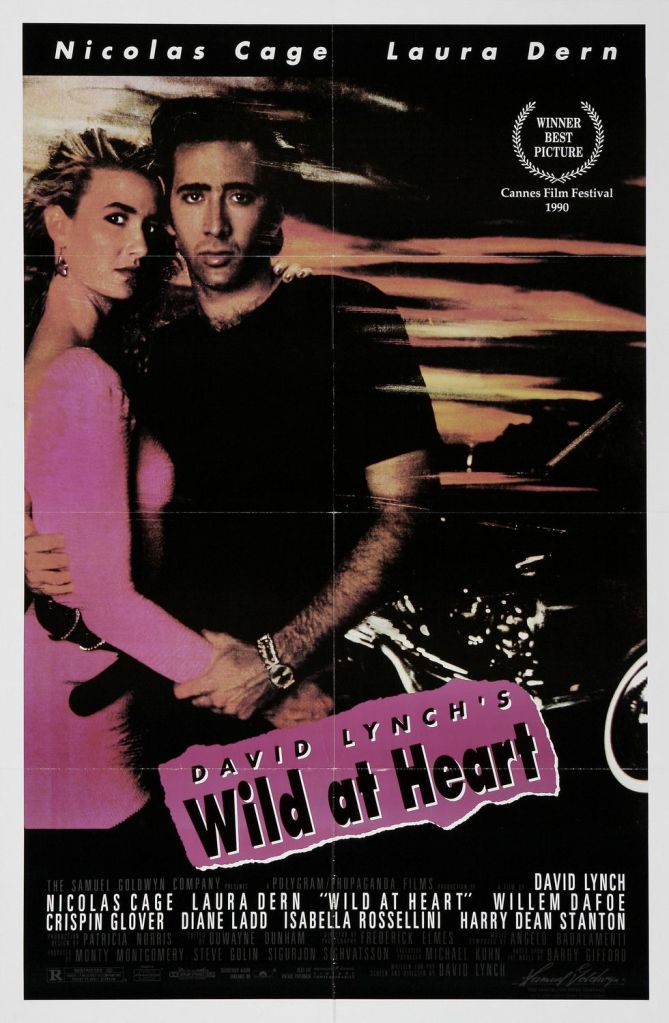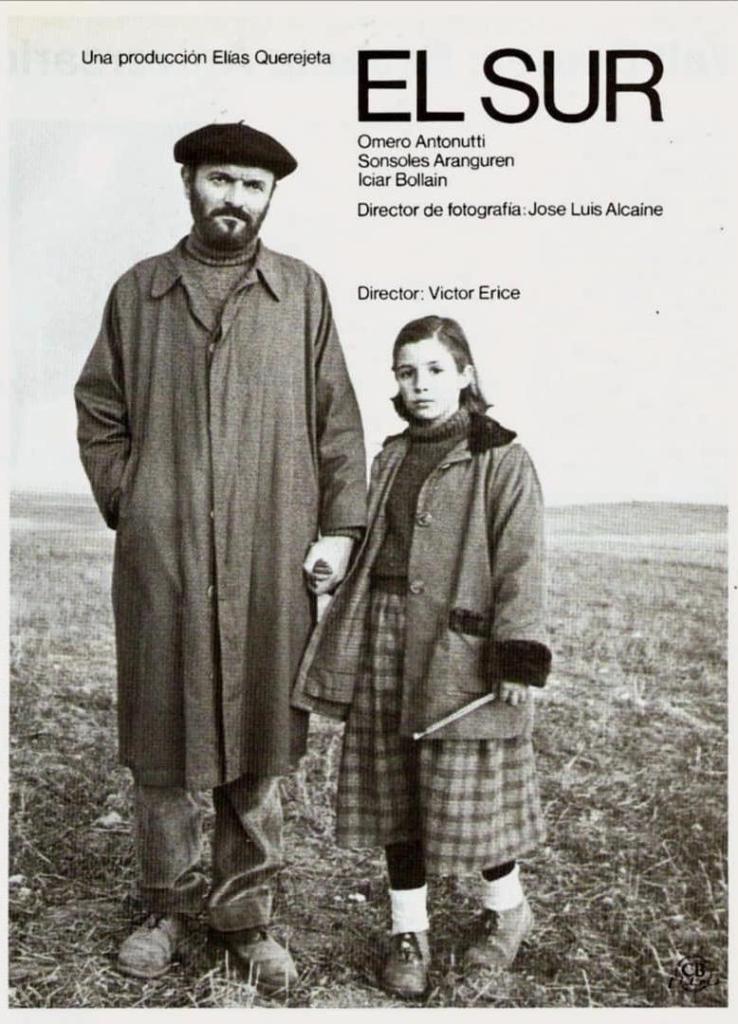(注:本文基于Vintage Books 1993年版本。我没读过中译本,故引用原文的中文部分是我自己翻译的。)
《英国病人》是那种读完了之后还会长时间地萦绕在读者心头的小说。这不仅由于它选取了二战为背景、对历史的钩沉带来一种神秘的未知,也不完全是因为两个穿插在一起的爱情故事的传奇性。至少于我而言,翁达杰对英语语言的精密探索和对现代人情感的深度发掘才是这本书吸引我的要素。
在读小说以前,我先看了明格拉执导的同名电影。看电影的时候,我赞叹它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但读了小说之后,我只能说完美是没有止境的。相比于影片实打实地呈现的北非沙漠和意大利古堡的浓烈景色,这本富于散文气息的小说则营造了一种自由、奔逸的阅读体会,在细致描写之中穿插着精心安排的留白空间,交予读者自行想象。这是我一直在好的作品里所期待的品质,作为一个文学热爱者,我认为语言所能给予的想像的疆域和强烈的身心愉悦是视觉永远比不上的。
一.作为迷宫的英语
《英国病人》是我读过的第一部翁达杰作品,暂时也是唯一一部。我不确定在他的作品谱系中,他具体的语言追求有哪些。可是我想他一定在通过这种散文化的小说写作探索语言的疆域。
散文化的气息首先来自于叙事的极端自由。在优秀作家的成熟作品面前,读者不常常能意识到叙事声音的存在——尽管一切故事都要靠叙事声音的讲述。翁达杰在做到这一点的同时,还可以轻易地在叙事结构的多个线索间自由转换。反复交错进行的正叙、插叙和倒叙,四个各具私人伤痛史的复杂人物,再穿插上北非的地理知识、沙漠里诸多流动部落的习俗、远古时期岩洞壁画的美学意义、排雷工兵掌握的技能、手枪的机械原理和不同口径手枪的性能……这是一部极其庞大的叙事体系。在读者所体验到的阅读的快感和获取相关知识的愉悦背后,是作者以他强大的控制力在对这些本来散乱无章的细节进行耐心的缝合。
比如,小说第一章在对Hana和Almásy的生活做了大致介绍之后(这里用到了一般现在时和一般过去时;时态也是关于这部小说大可研究的东西),以现在时叙述Hana阅读Almásy日记中关于沙漠中的风的段落。紧接着是Almásy直接对Hana讲述他在沙漠里坠机后被Bedouin部落所救的情节,叙述变成第一人称;然后又以过去时进行第三人称的叙事,描写沙漠部落如何利用Almásy的历史和武器知识。第一章结尾处又回到现在时的当下,也就是Hana离开了Almásy的房间以后。
类似的不同时态、不同叙事角度及人称之间的转换贯穿了整本书,营造了阅读经验中的一种立体感和交响感。当然,不是恢宏的交响乐的感觉,而是一首美妙的有着轻柔、忧伤主旋律的交响诗。我想,不这么写的话,读者似乎没法借由每个具体而微的动作、每个句子的语气和视角深入到人物的内心。
如此复杂的迷宫般的叙事结构却不会对阅读造成障碍,这是翁达杰文字的神奇之处。他没有让叙事的触角像八爪鱼一样触碰到每一人物的每一侧面,而是通过对叙事人称的细心选择,在遮与不遮之间,只让读者看到他想让我们看到的。在四个直接出场的主要人物中(Katherine几乎只出现在Almásy的叙述中,故不算在内),只有Almásy一人使用过第一人称,除此之外仅有一次,就是Hana在返回加拿大之前写给Clara的信中,也短暂地使用过第一人称。
Almásy的第一人称叙事主要用来叙述他和Katherine的爱情。在同名电影里引人瞩目的Katherine一角实际上到了小说的第142页才第一次出场,其后对于她的描写,大部分是通过Almásy之口。Almásy的过去对Hana和Caravaggio都是神秘的,他们一直想探究;Caravaggio甚至在Almásy主动选择死亡以前,通过不断给他注射大剂量吗啡的方式来诱导他进行回忆。因此Almásy的第一人称在书中构建了一个只有他和Katherine在其中的私密空间,Geoffrey Clifton和Katherine相继死后,这个空间就已彻底封闭,只有Almásy一人能够对它一次又一次地回访。Almásy在第一人称的叙事中坦白、无所不谈,但私密性就隐藏在这种表面的坦白之下,它制造了Katherine与Almásy的爱情的神秘性质,跟Hana和Kip之间的年轻、循序渐进的爱情模式形成了对比。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渐渐放弃了通过区别不同时态来分辨事件发生的时间的努力——这种努力从最初也许就不该有。城堡和沙漠是非常不同的两种场所。前者是建筑,石头围出了一个“内部”;后者是开阔、露天的。被废弃的城堡和北非沙漠唯一的相似之处,是荒凉。在这象征了战后人们心灵废墟的两个荒凉的空间里,时间的存在还有意义吗?我想这是翁达杰用尽英语的所有时态、用碎片化的叙事所提出和回答的问题。
在翁达杰笔下,《英国病人》中的英语成为了一座迷宫,每一堵墙都是他用被他解放了的语言所搭建的。而他作为一个操纵着拉线木偶的技艺高超的艺人,从始至终沉默地躲在文字后面,藏在了迷宫的最深处。
二.爱的神秘和精神性
在小说所涵盖的时间里仅仅存活在Almásy的讲述中的Katherine,是书里重要角色中唯一没有被写到心理状态的人,显然这是由Almásy的第一人称叙述所决定的,但作为一个事实,它凸显了Katherine这一人物的神秘性。
小说里的Katherine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女性,这与电影中Kristin Scott Thomas扮演的看上去已至少三十多的Katherine很不同。当我们必须在电影里面对一个身材细瘦、面部骨骼清癯的Katherine,翁达杰以几近写意的方式为读者描绘了一个年轻、有着良好阅读品味和艺术鉴赏力的Katherine。没有对外貌和身材的描写,即使是在Almásy的描述中,首先打动他的也是声音而不是形象。Clifton夫妇飞抵沙漠三天后的晚上,Katherine在一场篝火聚会上朗诵了一首诗,她的声音使Almásy燃起了爱的火焰:
“That night I fell in love with a voice. Only a voice. I wanted to hear nothing more. I got up and walked away. ” (p.144)
(那天晚上我与一个声音坠入爱河。仅仅是一个声音。我不想听到其他的东西。我站起来走开了。)
Almásy本来是不喜欢诗歌的,直到那晚他被Katherine背诗的声音所打动。诗歌借助声音,成为他们爱情的浪漫介质,也预示了这种爱情的精神含义。同时,语言——或者说交谈——成了二人沟通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不论他们的肉体达到了什么样极致的亲密程度,也都只是精神和灵魂上的互相缠绕的一种延伸。
Almásy曾经问Katherine:“你最恨什么?”Katherine说:“谎言。”而Almásy对同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所有权。”可是之后我们看到,痛恨所有权的Almásy被爱火炙烤得几近疯狂,对Katherine的占有欲使他常在公共场合因无法自控而出丑。他不但在心中生出了全部占有Katherine的欲望,而且他自己也变成了爱的奴隶,完全为爱情所占有。Katherine在Almásy的疯狂中感到害怕,决定终止这份感情。他们的告别发生在开罗的植物园里。一个雨水刚刚在树叶上被月光蒸发掉的夜晚,告别的拥抱过后Almásy已经走开,却又转身回来,说:“我只想让你知道,我还没开始想念你。”痛恨谎言的Katherine只是简单地说:“你会的。”(p. 158)
读者只能借由不同段落的提及来拼凑Katherine的形象。基本上可以知道她是一个来自英国的世家女子,受过完备的人文教养、毕业于牛津大学,而且这些信息也大都来自Almásy的揣测。此外,就只有一片又一片的空白需要读者在想像中自行联结。事实上,在Almásy和Katherine的关系中,不仅Katherine神秘,他们两人的爱情也是神秘的。建立在抽象的声音、交谈和精神交流基础上的感情,必然是如空气一样,可以被真切地感知,但不能被看见。
Almásy和Katherine从未探究过对方的历史。就像Almásy在沙漠中探险的十几年对Katherine是一个谜,Katherine在遇到Almásy前的一切人生经历,Almásy也并没追问过。但他们带着各自的历史,相遇且相爱了。这是一种最迷人、纯粹的爱情,我仿佛看到他们的人生旅程在他们各自身后汩汩流动,他们阅读过的书、行走过的地方、抚摩过的壁画、研究过的地图、探索过的沙漠……都构成了他们的那时那刻;坠入爱河的是两个那时那地的人,但与此同时,互相爱慕的其实还有不能够显性的历史和历史——他们都喜欢的书是希罗多德《历史》,似乎已暗示了这一点。所以,这是我在文学作品里看到过的最为成熟和厚重的爱情。
谈到这里不免还要提一下同名影片。我之所以认为电影的深度无法与小说媲美,一个原因是它过于强化了Almásy和Katherine的爱情——而事实上他们的爱只是故事的主线之一。并且电影增加了俗气的细节,但去掉了一些沉默和深刻的。举例说,在电影里,当Almásy历尽艰难又回到了the cave of swimmers(游泳者岩洞),发现Katherine已死,她身边的《历史》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着:“亲爱的,我很冷,手电也快没电了……”Almásy抱起她走出岩洞,失声痛哭。这个情节在书中完全不同,Almásy的叙述是这样的:
“It is important to die in holy places……When I turned her around, her whole body was covered in bright pigment. Herbs and stones and light and the ash of acacia to make her eternal.” (pp. 260~261)
(死在神圣的地方是重要的……当我把她翻转过来,她的整个身体都覆盖着明亮的颜料。草和石头和光以及树胶的灰烬使她永恒了。)
没有煽情的“我很冷”,也没有痛苦的仰天长啸,Almásy的回忆终止在了这里。他随之发表了对爱情的精彩看法:
“We die containing a richness of lovers and tribes, tastes we have swallowed, bodies we have plunged into and swum up as if rivers of wisdom, characters we have climbed into as if trees, fears we have hidden in as if caves. I wish for all this to be marked on my body when I am dead.” (p. 261)
(我们的死包含着爱人和部落的丰富性;包含着我们曾吞下的滋味;包含着我们曾进入且在其中游泳的身体,仿佛它们是智慧的河水;包含着我们曾攀爬进入的文字,好像它们是树;包含着我们曾经藏身其中的恐惧,犹如洞穴。我希望在我死时,所有这些都会烙印在我的身上。)
这样的文字,是让人忍不住想把书捂在脸上深深吸进它的气息的。这段话也证明,Almásy和Katherine的爱情的确只能发生在沙漠里,它是历史的沉默爱恋,不需要其他背景;而它的纯粹性最终导致了它的破灭。这份爱的极强烈的精神性还体现在,他们的爱情没有终结在荒凉的沙漠里,也没有终结于Katherine的死亡,却只能终结在Almásy停止回忆的时刻。
三.逃离与反思
作为对照,Hana和Kip之间的爱情是循序渐进的。他们的感情大部分也是建立在语言的沟通上,但与Almásy和Katherine不同的是,他们沟通的方式是互相给对方讲述自己遥远的家乡和各自的记忆。远离故土的两个人,一个来自寒冷的加拿大,一个来自炎热的印度,东方和西方在他们的爱情中相遇了。对Kip来说:
“All through his life, he would realize later, he was drawn outside the family to find such love. The platonic intimacy, or at times the sexual intimacy, of a stranger. He would be quite old before he recognized that about himself, before he could ask even himself that question of whom he loved most.” (p. 226)
(他将来会意识到,在他的整个一生,他都被引到家庭以外去追寻这种爱,这种来自陌生人的柏拉图式的亲密,或有时候性的亲密。在他认识到关于自己的这一点以前,在他甚至可以问自己他最爱谁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很老了。)
Kip所追求的爱不局限于男女之情。在他刚刚跟培训他排雷的上级和老师建立起一种父子般的亲密关系时,这位老师——英国人——在一次拆弹行动中牺牲了。这个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在二十岁的Hana这边,情况类似。她的父亲和恋人在她赴欧洲参与战争救护期间相继去世,她本人也流产失去了一个孩子。因此,他们两人在亲密关系中想要寻找的是一种情感上的支持,这也是为什么在他们的关系中,交谈占了那么大的比重。
大部队撤退的时候,Hana自愿要求与严重烧伤、不便行动的Almásy留在这座佛罗伦萨附近的废弃古堡,而这恰好也如Almásy所愿——身心内外皆受重创的他,早已对生活失去了渴望。在他们之后来到这里的Caravaggio,也是带着重创后的身心——他因在战争中做间谍而被德国军队俘虏并削去两手的大拇指。
背负着重重伤痛的四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残缺的。Hana和Kip是心灵上的残缺,Almásy和Caravaggio则是身心皆残。这四个残缺的人,守在一栋被一拨又一拨的敌我军队利用过后又废弃的古堡里,本来是为了逃离外面的世界——它使他们受了伤,他们不想再面对那个战争虽已完结、但满目皆是疮痍的同样残缺的世界。可是他们根本逃不脱,每个人都被自己的伤痛记忆所追逐,于是这才有了Kip和Hana的互相倾诉、Caravaggio对Hana的诉说,以及Almásy对自己在战争中的沙漠经历的讲述。古堡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牢笼,笼罩着他们的伤痛史。在古堡里,似乎他们的行走和一举一动,都跟随着记忆的阴影,它是痛过之后的又一重剧痛。
四人之中,只有外向型的Caravaggio会通过激烈的行为和言语来发泄对生活的厌弃和绝望。其他的三个人,除彼此之间平静的倾诉以外,都只是在城堡里静默地活动,想通过时间来忘却伤口。但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他们甚至从没特别地进行过什么努力。
城堡里困顿挣扎着的四个人的平静最终被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的消息打破了。对西方文明的失望困扰了Kip,在狂怒和激动中,他把枪口对准了他以为是英国人的Almásy。Caravaggio告诉Kip:“他不是英国人。”Kip却说:
“American, French, I don’t care. When you start bombing the brown races of the world, you’re an Englishman. You had King Leopold of Belgium and now you have fucking Harry Truman of the USA. You all learned it from the English.” (p. 286)
(他是美国人、法国人,我都不在乎。当你开始轰炸世界上的有色人种,你就是英国人。你们有过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现在你们有该死的美国人哈利·杜鲁门。你们都是从英国人那儿学的。)
来自印度的Kip对西方文明的信心崩塌了,他原本在他老师的身上建立的对印度的宗主国英国的一点信心彻底破灭了,哪怕他和Hana的爱情也无法挽救这颗受伤的心所经受的又一次重创。Kip骑上摩托车冲出古堡,逃离了战后的废墟,也逃离了西方文明。
与电影不同的是,小说并没有交代其他三人的结局(除了通过Hana的信,我们知道她想返回加拿大),故事直接跳到了许多年后的印度,在对Kip生活的描写中结束了整本书。Kip在狂暴中质问Almásy时曾谴责:
“Your fragile white island that with customs and manners and books and perfects and reason somehow converted the rest of the world. You stood for precise behaviour. I knew if I lifted a teacup with the wrong finger I’d be banished. If I tied the wrong kind of knot in a tie I was out.” (p. 283)
(你们有着传统、规矩、书、圆满和理性的精巧的白色的岛,莫名其妙地改变了其余的世界。你们代表了正规的行为。我知道如果我用错误的方式举起一个茶杯,如果我在领带上打了一个错误的结,我就会被驱逐。)
从这里可以看出,Kip对西方文明的质疑并不是一时而起,它早已在Kip的族群身上积累了世世代代。当他骑在摩托车上驶出那座古堡,其他三个残缺之人,三个携带着历史、记忆和伤痛的幽灵的西方人,被他留在身后,留在了犹如牢笼的古堡中。十多年后,对Kip在印度家中的桌边,是这样的描写:
“At this table all of their hands are brown. They move with ease in their customs and habits.”
(在这张桌子上,所有人的手都是棕色的。它们在自己的传统和习惯中自如地移动。)
我不确定生于斯里兰卡的翁达杰本人是否有印度裔的血统,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故事的结尾处,同为棕色人种的翁达杰和Kip的身份重合了。读到这里,才终于能够确定,尽管书中使用了第一人称视角的只有身为匈牙利人的Almásy,故事的落脚点却是东方人对西方文明的反思。作为小说标题的“英国病人”并不只呼应了重度烧伤的Almásy被误认为是英国人这一情节,而是也指出了“英国”之“病”。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象征了西方的现代文明,所以在这个故事的内部,其实隐藏着居住在加拿大的斯里兰卡人翁达杰对战争之后正在倾塌的西方文明的忧虑。
翁达杰用他恣意挥洒、跨语体跨人称跨时态的英语写作表明,语言的表现力是没有边界的。在看似迷宫而实则无疆界的广大领域内,《英国病人》这部小说容纳了星空般广阔的内容。那触动人心、灵肉交缠的爱情,那些深渊般令人目眩的深刻情感,都是历史和文明在挣扎。在大时代的背景下临渊自照,是谁会看到遥远的东方隔海发出声声感叹,叹息那个他曾经的恋人留在了旧时代、旧习惯里,就像Kip对Hana的最后的想像。
李沁云
2013年3月初稿写于泽西城